分离批判
影片信息
- 状态:HD中字
- 主演:居伊·德波/Caroline Rittener/
- 导演:居伊·德波/
- 类型:短片/
- 年份:1961
- 地区:法国/
- 语言:法语
- 上映:未知
- 时长:18分钟
- 更新:2024-04-18 19:57
- 剧情:
扫一扫用手机访问
为你推荐
换一换-
720P阿尔巴·布吕内,Raquel Ferri,贝茜·特内兹,Alejo Levis,佩普·安布罗斯,Sara Diego,Charlie Pee,Clara Altarriba,鲁姆·巴瑞拉,Daniel Lumbreras
-
720P内详
-
HD坦莫伊·达纳尼亚,Sahil Mehta
-
2.0HD1280高清中字版马东锡,金敏载,李圭成,朴智焕,李奎浩,李晟宇,차우진,李泰圭,이상용,아이락 김
-
3.0高清谭渤霖,于菲菲,张斯斯
-
高分推荐HD中字8.1 龚蓓苾,吴超,李易祥
-
HD中字大卫·马佐兹,莉莉·奇,Eli D Goss,Jolie Curtsinger
-
高分推荐HD9.3 Douglas Keay,Wilfrid Thomas
-
9.01080PAlexa Leigh Fletcher,Brooke Wallace
-
高分推荐1080P8.2
精彩评论
-

少语多肉回复错失的相遇:在暴动与“年轻女孩”之间的分离批判
2023-06-23 15:38:29转发自公众号:NomadMaster
翻译/布雷松
例如,这部电影的最后几分钟由情境主义国际(SI)成员的一系列照片组成,并伴有德波的画外音独白。独白的最后部分澄清了这是一部没完没了的电影,伴随着画外音,影片的导演德波和真正的制片人阿斯格·乔恩之间的眼神对视镜头,就像他们在对话一样。[②]正如德波所说的《分离批判》是“一部自我打断但永远不会结束的电影”,这部影片的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被迫阅读一系列字幕,就好像德波和约翰的文字记录一样。编辑室里的私人谈话。[③]其中一个字幕在屏幕上闪过,就像乔恩盯着我们看的画面一样,它声称我们正在看的电影——因为我们看的不是电影本身,而是一个后置镜头,一个脚注或附录——关于私人生活,所以“只有一部关于‘私人生活’的电影才会完全由‘私人笑话’组成。”[④]所以,我们需要推测这实际上是一个笑话:“我们制作了改编成时长3个小时的纪录片系列,是《异化的纽约之谜》系列[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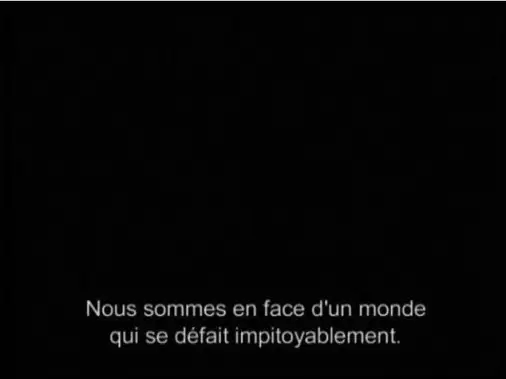
[2]Jorn专门成立了Dansk-FranskEksperimentalfilmkompagni公司为德波拍摄电影。
[3]GuyDebord,Critiquedelaséparation[电影剧本],inOeuvres(Paris:Gallimard,2006),552。本文中所有对德波手稿《分离批判》的引用均来自“Oeuvres”,541-555.我自己翻译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断断续续》实际上是一部影片的时长不是由内部叙事或格式决定,而是由胶片库存耗尽决定的。
《纽约之谜》是默片时代红极一时的《伊莲的故事》的法语翻译,其中由珍珠白饰演的女主角无情地追捕一个神秘的反派,这个反派杀死了她的父亲,并被人们所熟知。迷人的绰号“紧握的手”。和《分离批判》一样,该剧的剧集比通常的故事片要短得多,分成几集,这样就可以一周又一周地播放,每集的结局——实际上,不是结局——都会留下悬念。这个最初提出的标题可能是一个个人玩笑,暗指德波对媚俗和文化产品的暧昧品味,1958年与乔恩合着的书《回忆录》就证明了这一点,该书几乎完全由科幻小说、漫画、图画小说组成,以及黑色系列的侦探小说。对无声电影时代系列电影所使用的过时利基形式的提及也表明,这种对历史形式的回归一旦重新激活,就可以用来揭开当代纪录片的神秘面纱。[⑥]如果这是不经意间与不久的将来之间的一种点头,那也算是一种先见之明,因为连载的形式将不再适用于电影,而是适用于竞争日益激烈的媒体电视。[⑦]我们当然应该逐字逐句地理解这个笑话,但我们应该考虑到1959年德波系列短纪录片的想法——《分离批判》是《异化纽约之谜》系列的第二集”,第一集是《关于在短时间内的某几个人的经过》(Surlepassagedequelquespersonnesàtraversuneassezcourteunitédetemps,1959)——不仅是一部纪录片,也是一部犯罪或谜题。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注释:在这种情况下,犯罪的关键问题不再位于叙事时间,或分配给单个机构。犯罪的关键问题不再是这起或那起谋杀;而是指谋杀。这不是“特殊的过错”,而是早期卡尔·马克思所称的——德波在另一段话中引用的——异化或说“分离”的“绝对过错”[⑧]。
[6]默片时代的系列电影中,《纽约谜案》对于超现实主义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点,在这次交流中无疑暗示了一种偏好。参见罗伯特·德斯诺斯,《Fantômas、LesVampires、LesMystèresdeNewYork(1927)》,《法国电影理论与批评:1907-1929》,编辑。理查德·阿贝尔(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398–400.
[7]德波的电影在某些主题上引用了电视。电影《景观社会》中,很多片段取自电视和央视。在《游荡在夜的黑暗》第一章中,现代社会的劳动者被表现为看电视。德波临终时参加了一部电视纪录片:《居伊·德波:他的艺术和他的时代》。
[8]在马克思1844年版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引言中,我们发现现代无产阶级是“一个公民社会阶级,而不是一个公民社会阶级,一个所有身份都消解于其中的阶级,一个由自己决定的群体”。通过共同的遭遇来拥有普遍的品质,并声称没有特殊的权利,因为没有特殊的错误,只有普遍的错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文集,卷。3(纽约:国际出版社,1975年),186;原文强调。德波推翻了这段话,并在《景观社会》114中写道:“无论是数量上的贫困改善,还是阶级融合的幻想,都不能持久治愈其不满,因为无产阶级既不能真正了解自己,也不能真正了解自己。”在它所经历的特定不公正中,因此不是在纠正特定的正义,也不是在大多数不公正中,而只是在生活边缘被抛弃的绝对不公正中。在正义中真正认识自己。”居伊·德波(GuyDebord),《景观社会》,作品集,816;强调原创。
这还不是全部。《分离批片》在作为一部关于“私生活”和悬而未决的犯罪故事的纪录片的同时,它也将自己呈现为一个陈词滥调的爱情故事,其中神秘的女主角可能与电影《伊莲的故事》相呼应,而且也更类似于安德烈·布雷顿的小说《娜嘉》。结合德波的所有电影,《分离批判》中的大部分素材都是从新闻片、广告或平面媒体等来源借用或脱轨的视频片段。但与他的其他一些电影不同的是,尤其是1973年制作的最广为人知的电影版本《景观社会》(《景观社会》,1974年)和1978年制作的《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然后被烈火吞噬》(1978年)——这部德波电影from1961没有使用电影史上的镜头。相反,德波将他挪用的穿着比基尼的年轻女性、刚果骚乱和美国战机扫射的镜头组织成一个明显虚构的叙述,其中摄影师安德烈·穆奥盖斯基·姆鲁加斯基(AndréMuogeskiMrulgaski)的35毫米镜头显示了德波——或者他自己扮演的“角色”——跟踪一个年轻的女孩。女孩穿过巴黎街头。有时她会闪过镜头,安装在行驶中的汽车上的摄像机会短暂地捕捉到她的身影,就像电影的开场预告片中那样;声音被德波强加的独白带走(就像在旧的无声电影中一样)或被挤出,这也不是对她说的,而是对电影观众说的。虚构电影的叙事惯例迫使我们将作为电影制片人的德波与作为电影画外音解说的德波区分开来,并与电影中德波所扮演的“人物”区分开来: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追求着自己的梦想。17岁左右的年轻女孩。这种虚构范式中的精确区别是复杂但必要的,因为在电影中的某个时刻,我们看到德波真正的妻子米歇尔·伯恩斯坦(MichèleBernstein)陪伴着这位年轻的女孩,她是SI创始成员中唯一的女性,她出现在电影中就好像她是故事的一部分,扮演着皮条客、诱惑者或竞争对手的角色。在《德波》拍摄这部电影期间,伯恩斯坦写了两部小说,它们不是特定的文本(如《德波》所写的《回忆录》),但属于《SI》的整个流派和惯例。[9]如果我们考虑到她的故事以18世纪经典的三角恋文学主题为中心,我们就不得不为影片明显的虚构层面的模糊性寻找方向:我们意识到《分离批判》虽然电影记录了德波(或者可能)伯恩斯坦对这个在电影中聚集了如此多能量和注意力的年轻女孩的真实诱惑,制作电影本身的行为就是他们用来诱惑女孩的不在场证明,即他们的诱惑行为不是影片中模拟的。


这个年轻女孩是谁(或者她做什么)?在某种程度上,这才是影片想要追寻的真正谜团的问题。这个年轻女孩也在电影中说话(我们确实听到过),但不是在由爱情故事的虚构结构构建的故事的“现实”中。她的声音出现在影片的开头,背诵着语言学家安德烈·马丁内斯关于语言与现实“分离”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影片的题词。从《为萨德疾呼》(HurlementsenfaveurdeSade,1952)到《游荡在夜的黑暗中》,年轻女子或未成年女孩是德波所有电影中不变的主题。但在他的前两部电影《为萨德疾呼》和《短时间内的经过》中,年轻女孩(以及更普遍的青年和性别差异)不仅仅是一个主题参考,而且首先是与电影中其他声音的辩证关系。互动声音。例如,在《短时间内的经过》中,德波自己的声音,在电影的技术报告中被描述为“悲伤和压抑”,并不是唯一的声音,而是与其他声音一起表演的,其中一个被明确标识为“少女”的声音。[10]早期电影中的这种多重声音必然强调德波自己的声音是一种戏剧或虚构的构造,而不是一种理论或分析的特权地位。德波的声音是一种与其他人不同的声音,忧郁而自我放逐,不同于其他被定型为播音员的男声,也不同于标点符号般存在于其中的女孩声音。虽然两个男声占据了客观中立和主观抒情传统的两极,但女孩声音的这种转变风格(WechselderTöne)的确切位置却不太容易定义。这里的年轻女孩经常发出与她的声音和年龄相比显得不一致甚至讽刺的短信。例如,在一篇文章中,她提到了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并谴责了列宁所说的左翼共产主义的“幼稚”混乱——德波和SI都会认同这种混乱。政治倾向,尤其是1961年之后的时期。
[10]她在这些关系中的地位可以在德波1964年的《技术笔记》(Contrelecinéma)中找到。德波,作品,486。
《分离批判》从一开始就阐明了它的主题:失去。影片的开场以一个女人讲述失败的漫画结束,背景是一辆陷入沼泽的吉普车,德波在画外音中问道:“我们失去了什么真正的价值?”计划?”[12]这种形式的提问不仅强调了计划本身的失败或被外界强迫的失败,而且还强调了计划本身的性质和不确定性。在接下来的15分钟里,影片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主题,讲述失败的计划和迷失方向的冒险。从这个角度来看,《分离批判》确实可以看作是《短时间内的经过》的后续,而这部电影也聚焦于少数人未能完成他们在1952年制定的计划。当时,AlphabetistInternational刚刚已成立。《分离批判》特别强调损失以及损失与时间的关系:没有任何事件而分散的“空时间”(emptytime)、“失去的时刻”(lostmoment)和“浪费时间”以及更普遍的时间“溜走”,或者我们——德波、革命运动以及他的整个时代——让它“溜走”。“时间。时间就在那里,德波的画外音阴沉地继续着,但现在的时间,山水的时间,是这样组织的,每一次实际的相遇,每一个历史的时刻,都被错过了:“我们没有发明任何东西”,“我们什么时候错过了机会?”[13]


在剧本中比较抒情的一段话中——德波写的很多句子都是断断续续、断断续续、空洞的鬼语——我们发现这个主题与德波写作中的一个一贯的性格有关:不年轻的女孩,但是一个孩子,一个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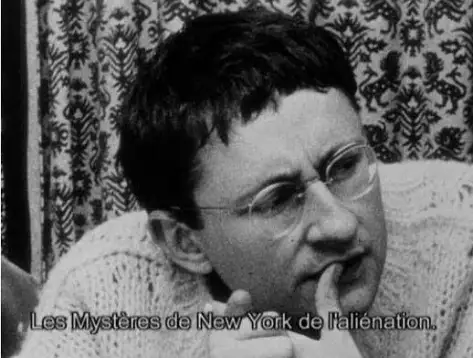
都是关于失去的范围——也就是说,我在流逝的时间里迷失了自己;因此,在社会意义上计划时间的粗俗意义被称为浪费时间——奇怪的是,在古老的军事表达中“像一个迷路的孩子”遇到了探索的领域,未知领域的领域。所有形式的探索、冒险、前卫。在这个十字路口,我们迷失了自己,也迷失了彼此。[14]
无论用什么样的基本观点来看待德波的一生、作品和政治,文森特·考夫曼用“迷失的孩子”这一主题来梳理德波所有作品的轨迹,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正确的。[15]Lesenfantsperdus(迷失的孩子)是军事意义上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些分遣队跑在正规军前面,通常在敌人战线的后方,知道他们的任务是致命的,他们必须独自战斗[“forlornhope”(绝望的希望/敢死队)这一表达的英文翻译失去了对“孩子”含义的参考]。[16]在对“lesenfantsperdus”的特别引用中,我想强调的是,相遇的概念与失踪或逃避矛盾地结合在一起:在这里,迷失范围的模糊轮廓被赋予了十字路口的具体形象十字路口,我们相遇,同时又失去彼此。这个十字路口或错过的相遇——一段莫名其妙地“迷失”自身的时间段——是电影和德波在想要象征事物时追踪年轻女孩(第一眼看到她是在电影第一个序列的十字路口)的嘴。
[16]这里的“希望”并非指英语语境中的相关含义,而是指荷兰语单词“hoop”,表达了“迷失的孩子”(verlorenhoop)的意思。在《分离批判》的当代文本《无条件抵抗》中,这位未署名的作者将战后法国城市的帮派与父母在革命后的内战中丧生的早期苏联孤儿进行了比较。战后的法国并不是在肉体上被父母抛弃,而是因为象征秩序的崩溃以及家庭和父亲的意识形态调解而被驱逐。在《游荡在夜的黑暗中》中,德波的画外音评论道,不再属于父母的孩子成为了景观之子,不再发挥象征秩序或调解的功能,对父母怀有怨恨情绪,将父母视为竞争对手而不是而不是作为可以依靠的人。参见Debord,“Défenseinconditionelle”,《国际形势》(巴黎:Fayard,1997年),211–213。
那么,什么样的“名副其实”的节目丢失了呢?《分离批判》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含糊:通过对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城市和更普遍的生存条件)“共同支配”的计划来实现资本主义秩序的一般论点。[17]对环境的统治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对使用价值生产的共同控制和管理,而在于对环境的共同统治矛盾地成为了德波继承的“真正的个体”的条件。马克思的一个陈述,更准确地说,实际上成为“真实个体”之间相遇的条件。[18]这些遭遇有一个情感名称,德波、文学家和早期情境主义者通常称之为“热情”。真正的邂逅使激情具体化的条件是一种共同的力量,可以“创造我们自己的历史”并自由地构建情境。“情境”一词指的是理性与偶然之间的交集或相遇。它描述了一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必须以合理的方式构建它,以便这种偶然的、真实的、切线的相遇成为可能。
[18]德波,《分离批判》,544。“真正的个体”是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个关键术语,德波在这里也提到了它。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对个人的压制,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相反,对自然的共同统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允许了“真正的个体”。这个“现实”的本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个体的现实并不是由某个机构整合成一个整体的构成,而是不同个体在时间上真实的相遇。
《分离批判》将奇观称为对这些精确相遇的程序性篡夺——基于分离的操作。在德波电影之后《SI》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AttilaKotanyi和RaoulVaneigem声称现代城市是围绕圆圈的逻辑组织的:循环是“相遇的对立面”[19]《分离批判》表明城市景观禁止真实个体之间的相遇,并用鬼魂或阴影困扰的事物之间的任意“交换”取而代之。[20]对于马克思和德波来说,共产主义是一种存在模式的名称,在这种模式中,对自然的共同统治为个人之间真实而热情的接触开辟了道路。但在这样的风景条件下,“有一些相遇”,德波的画外音再次响起